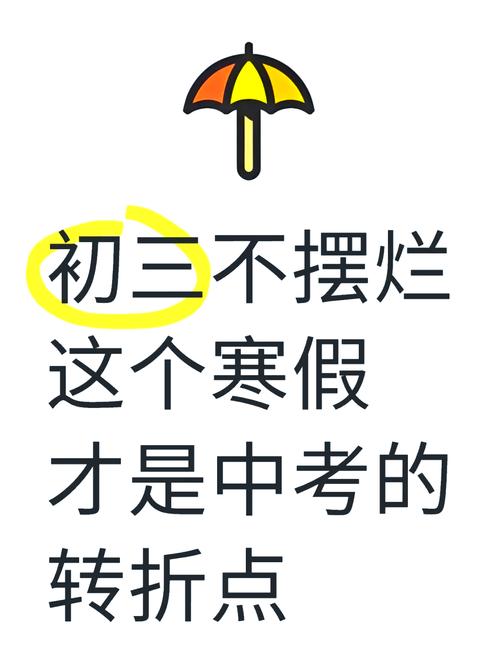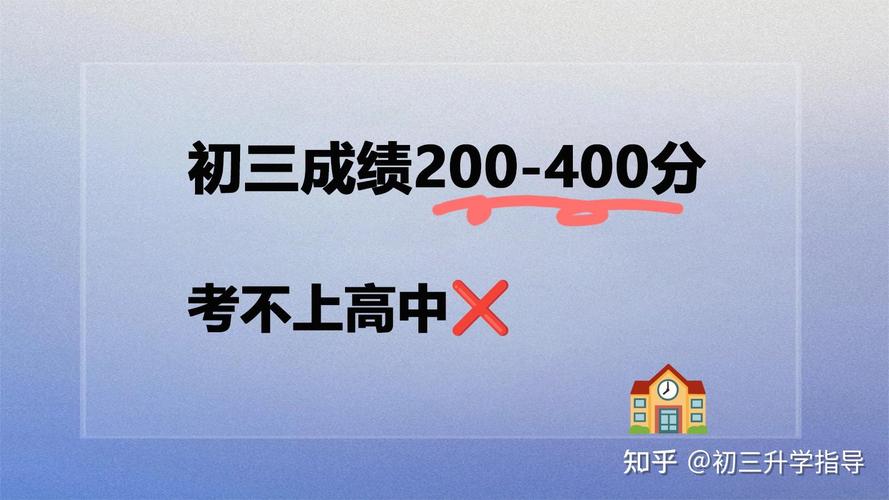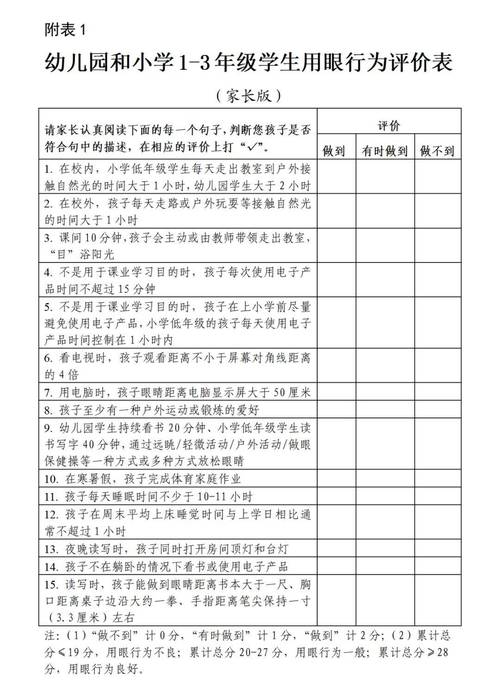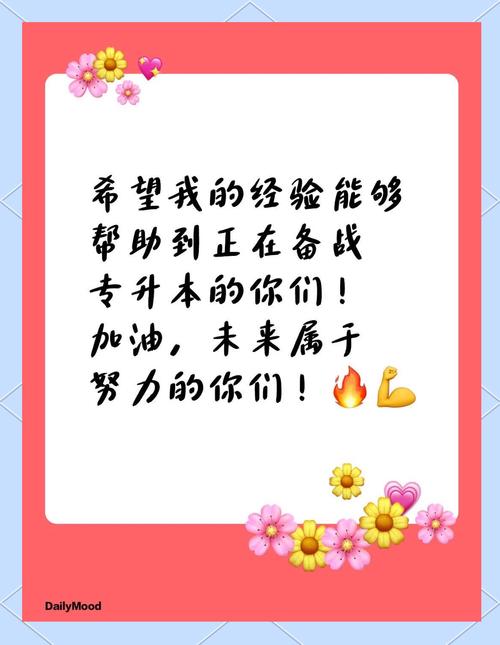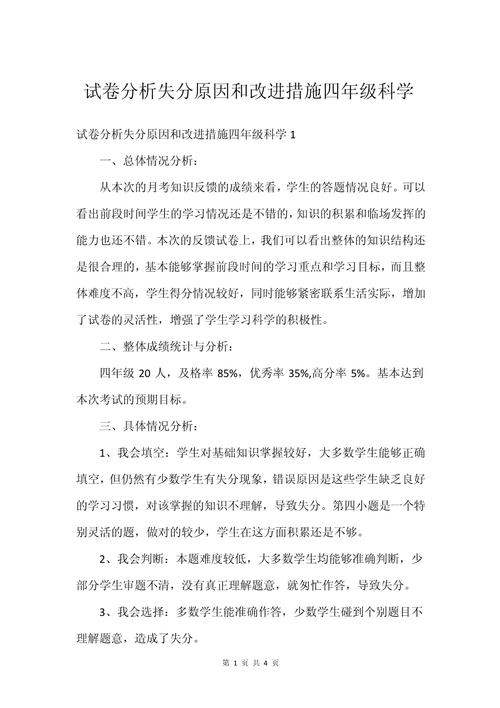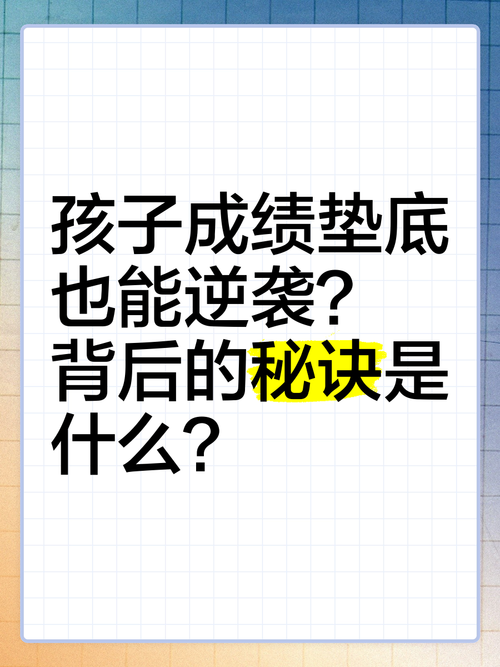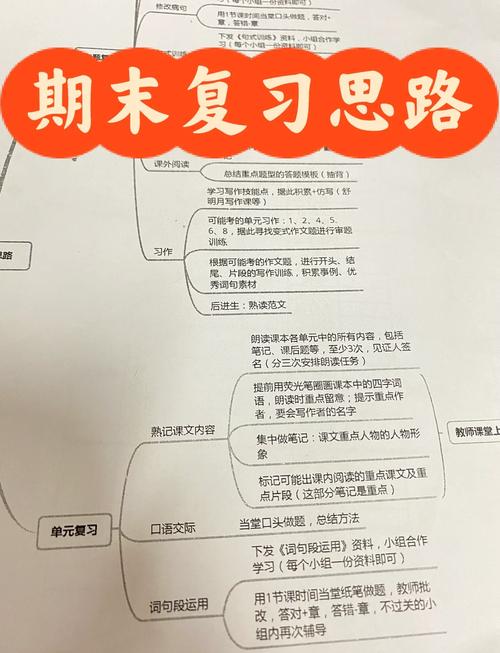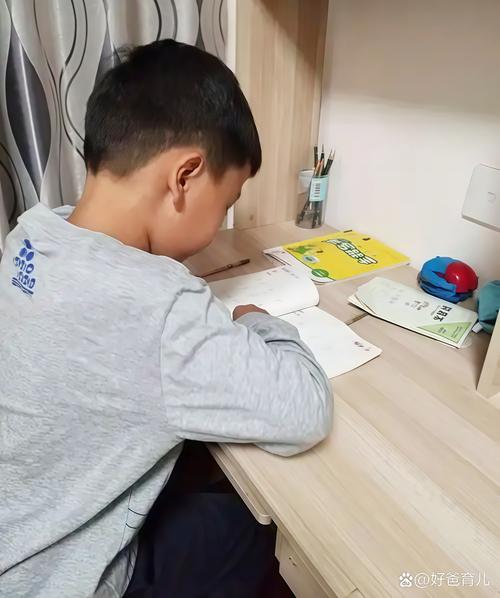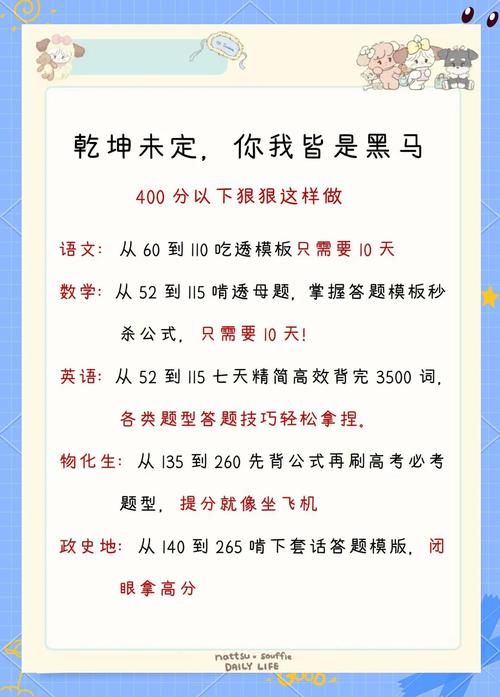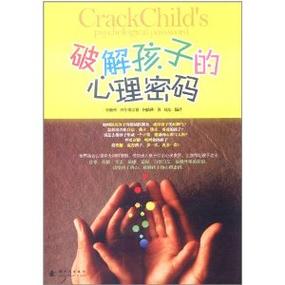1948年出版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作为丁玲创作生涯的首部长篇小说,犹如一面多棱镜,折射着20世纪中国文学转型期的多重光谱,这部诞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作品,既承载着解放区文学特有的政治使命,又隐含着丁玲对五四精神的艺术坚守,在政策导向与艺术自觉的张力之间,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肌理,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嬗变的窗口。
历史褶皱中的创作突围
1946年冬,丁玲随土改工作队进驻河北涿鹿县温泉屯,这段经历绝非简单的政策实践,对于这位始终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而言,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国乡土社会的契机,在冰封的桑干河畔,丁玲敏锐捕捉到社会结构裂变中的精神震颤——当千年地租制度轰然崩塌,不仅土地所有权在转移,人的尊严与价值体系也在经历着深刻重构。
这种观察视角明显区别于同期土改题材作品,不同于周立波《暴风骤雨》的阶级叙事范式,丁玲在政策框架内执着探寻人性的复杂光谱,小说中地主钱文贵被塑造成"开明士绅",这种处理方式既反映了华北地区土改的实际复杂性,也暗含着作家对简单二元对立模式的突破,在创作手记中,丁玲反复强调要写出"活生生的人",这种艺术追求使得作品超越了宣传文学的局限。
启蒙精神的隐性传承
细读文本可以发现,五四新文学传统如暗流般涌动在革命叙事之下,知识女性出身的作家,在塑造黑妮这个人物时倾注了特殊的情感投射,作为地主侄女却心向光明的形象设置,既是对阶级出身决定论的微妙质疑,也是对个性解放主题的当代转译,当黑妮冲破宗法桎梏走向新生活时,我们依稀可见莎菲女士的精神血脉。
这种启蒙意识的延续更体现在叙事策略上,小说采用多声部叙事结构,让农民、干部、地主等不同群体获得平等的话语空间,在斗争大会上,老农侯忠全颤抖着诉说苦难的段落,既是对封建压迫的血泪控诉,更是个体意识觉醒的文学见证,这种对"人的发现"的执着,使作品获得了超越时代的思想深度。
性别视角的叙事突围
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女性意识的作家,丁玲在革命叙事中悄然植入了性别观察,工作队女干部杨亮的形象塑造颇具深意:她既要执行政策指令,又要面对乡土社会的性别偏见,在动员妇女参加斗争会的情节中,作家细腻展现了革命话语与传统观念的激烈碰撞,那些躲在门后窃听的农妇们,她们的觉醒过程远比男性更为曲折艰难。
这种性别敏感在婚姻描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,当童养媳出身的董桂花获得婚姻自主权时,文本特别强调这是"政治解放带来的身体解放",这种将阶级革命与性别解放并置的叙事策略,既是对解放区妇女政策的文学诠释,也延续了丁玲早期创作中的女性关怀,在革命洪流中,作家始终没有放弃对女性特殊境遇的观照。
文学史坐标系中的多维价值
回到1948年的历史现场,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出版引发了两极评价,主流文坛将其奉为"延安文艺方向的典范",而胡风等人则批评其"政治性损伤了艺术性",这种评价分歧恰恰印证了作品的过渡性特征:它既是解放区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,也预示着建国后文学规范化的先声。
从更长时段考察,这部作品构成了丁玲创作转型的关键节点,早期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中的个人主义呐喊,在此转化为集体叙事中的个性坚守;中期左翼小说中的革命激情,在此沉淀为对历史变革的理性观察,这种创作轨迹,某种程度上映射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嬗变的典型路径。
当我们将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谱系中审视,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土地改革的历史场景,更在于展现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复杂可能性,丁玲以艺术家的敏锐,在政策框架内开掘人性的深度,在集体叙事中守护个性光芒,这种创作姿态对当下文学创作仍具启示意义,在桑干河粼粼的波光中,我们既看到了太阳照耀下的土地新生,也窥见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时代洪流中艰难求索的精神轨迹,这部作品如同河床上的鹅卵石,经岁月冲刷愈发显现出其独特的文学质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