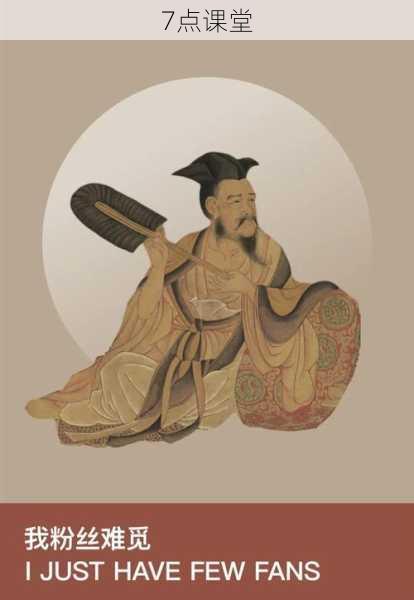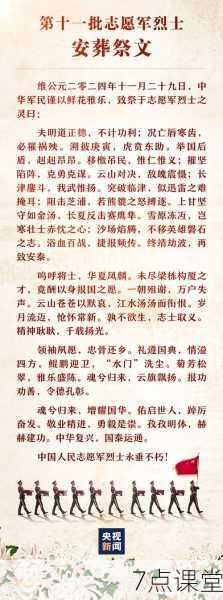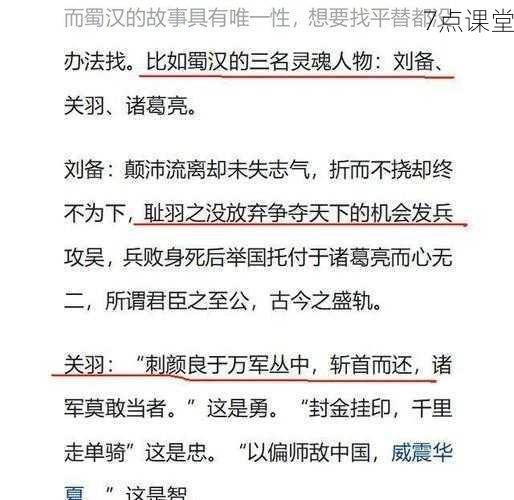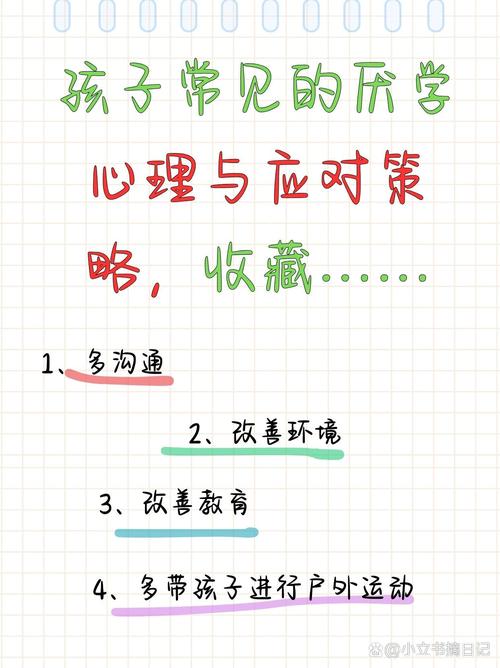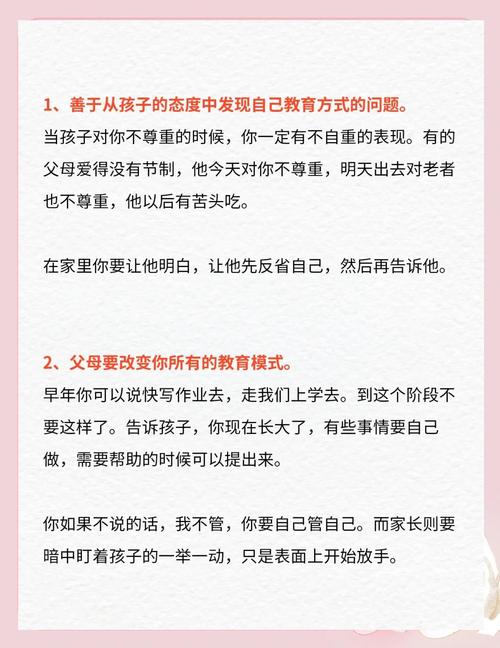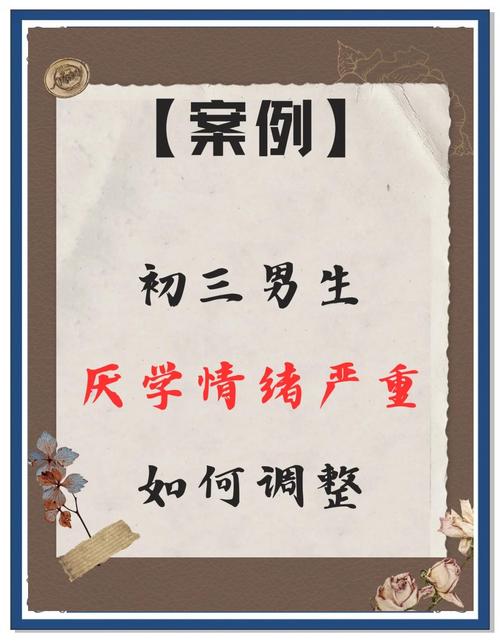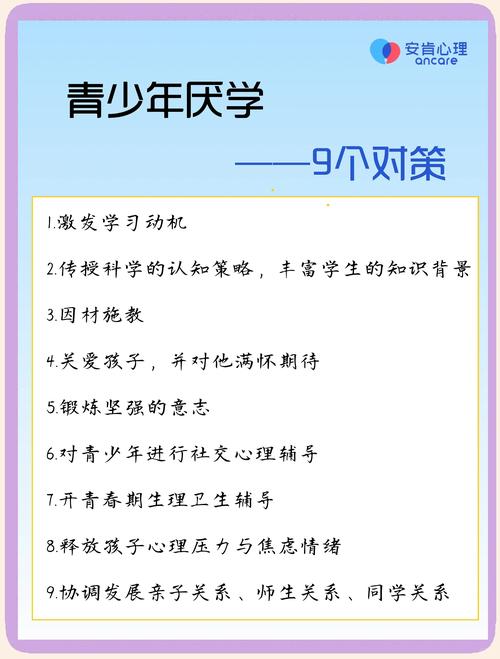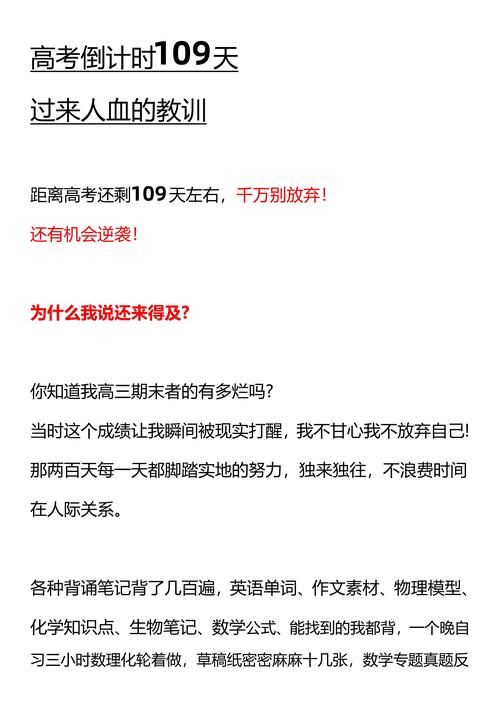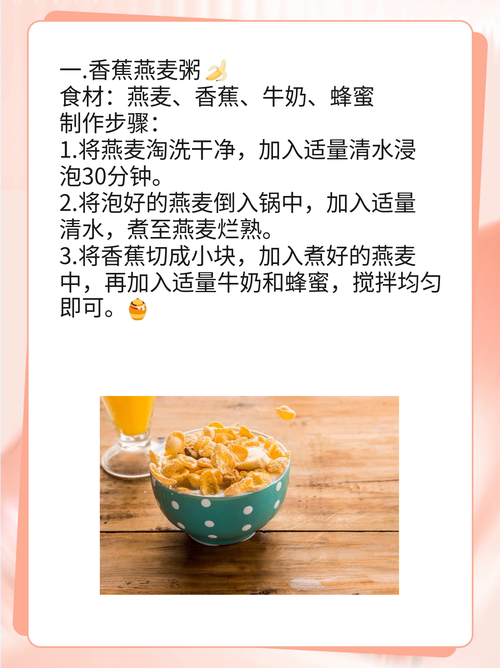公元3世纪中叶的一个黄昏,广武山残阳如血,酒意微醺的阮籍踉跄登上这座楚汉古战场,对着苍茫暮色掷出一句惊世骇俗的慨叹:"时无英雄,使竖子成名!"这句被后世反复咀嚼的狂言,犹如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,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,当我们试图拨开千年迷雾,探寻阮籍口中的"竖子"所指何人,实际上是在触摸魏晋之际文人群体复杂的精神世界。
历史语境中的双重投射
阮籍的狂言记载于《晋书·阮籍传》:"尝登广武,观楚汉战处,叹曰:'时无英雄,使竖子成名!'"这座见证过刘邦项羽对决的古战场,在魏晋时期已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地标,表面上看,阮籍的叹息似乎直指楚汉相争的胜利者刘邦,这位出身市井的汉高祖,在传统儒家叙事中常被塑造为"天命所归"的圣主,但在崇尚名士风骨的魏晋文人眼中,却可能沦为投机取巧的"竖子"。
然而细究阮籍所处时代,这句话更可能暗藏双重历史投影,司马氏集团正通过权谋手段逐步蚕食曹魏政权,这种"以诈取天下"的路径与刘邦当年何其相似,阮籍好友嵇康在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痛斥的"礼法之士",恰与刘邦"不事生产"的痞子形象形成微妙呼应,这种跨越时空的类比,使得"竖子"的指涉既指向历史又暗讽现实。
身份解构中的价值重估
东汉以降的士族社会,逐渐形成以门第、德行为核心的价值评判体系,阮籍作为陈留阮氏子弟,身处士族集团却对主流价值观保持疏离,他在《大人先生传》中塑造的"超世而绝群,遗俗而独往"的理想人格,恰与刘邦这类实用主义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。
魏晋之际的"英雄"标准正在发生深刻嬗变,曹操作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自称"乱世英雄",刘备被许劭评为"枭雄",这种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突破,在阮籍看来或许正是世无真英雄的体现,史学家余嘉锡在《世说新语笺疏》中指出:"嗣宗(阮籍)此言,盖以英雄自命,而叹时无刘、项,遂使刘邦之辈得成其名耳。"这种解释揭示了魏晋文人独特的价值坐标系。
文化心理的深层隐喻
阮籍的叹息不能简单视为历史人物的臧否,在《咏怀诗》第八十首中,他写道:"出门临永路,不见行车马,登高望九州,悠悠分旷野。"这种天地苍茫的孤独感,与广武山上的慨叹形成精神共鸣,所谓"竖子",实则是阮籍对现实世界价值颠倒的总体性批判。
值得注意的是,阮籍曾担任东平相、步兵校尉等职,这种"形在庙堂,心在江湖"的矛盾状态,使其批判更具复杂性,正如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所言:"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,不过是用以自利...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,亵渎了礼教,不平之极,无计可施,激而变成不谈礼教,不信礼教。"这种精神困境,恰是"竖子"之叹的最佳注脚。
话语建构中的历史记忆
自唐代刘知几《史通》质疑阮籍"此言竟未详所指"以来,历代学者对"竖子"身份的解读形成两大流派,苏轼在《东坡志林》中力主指刘邦说,认为"竖子指汉高祖";而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则认为"曹孟德挟天子,令诸侯,是亦一竖子也",这两种观点的对立,折射出不同时代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差异。
现代学者田余庆在《东晋门阀政治》中提出新解:阮籍所言实为双关语,既讽汉高祖得天下之易,又刺司马氏谋国之奸,这种解释将个人话语置于时代变局中考察,更贴近魏晋之际"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者"的历史语境。
文化符号的现代启示
阮籍的"竖子"之叹历经千年仍具生命力,因其触及了永恒的价值命题:何为真正的英雄?在功业与道义之间如何取舍?当我们在当代社会重审这段公案,不应止步于考据辨伪,更要关注话语背后的精神抗争。
在《晋书》记载的场景中,阮籍说完这句话后"退而著《豪杰诗》",这部失传的著作或许包含着他心中"英雄"的真正标准,今天重访广武山遗址,虽不见当年战阵烽烟,但阮籍独立苍茫的身影,依然昭示着知识份子在历史洪流中的精神坚守。
穿越时空的迷雾,阮籍口中的"竖子"究竟是谁已不再重要,重要的是这句狂言揭示的深刻历史辩证法:当价值体系崩塌之际,任何成功都可能是可疑的,在魏晋这个"人的觉醒"时代,阮籍用醉眼朦胧的目光,看透了权力游戏的本质,这种清醒的痛苦,恰是中华文化中最具震撼力的精神遗产,当我们再次吟咏"时无英雄,使竖子成名"时,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:真正的英雄,永远在价值坚守与历史宿命的夹缝中寻找出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