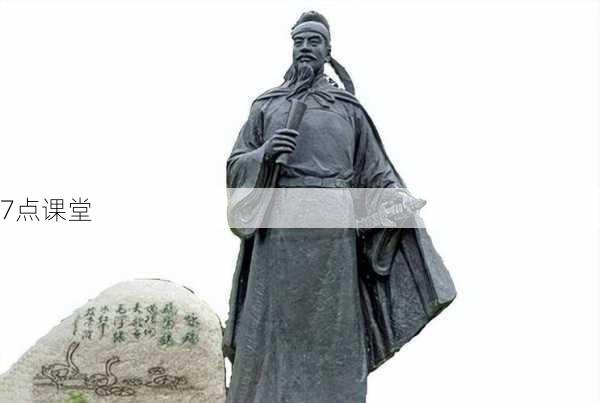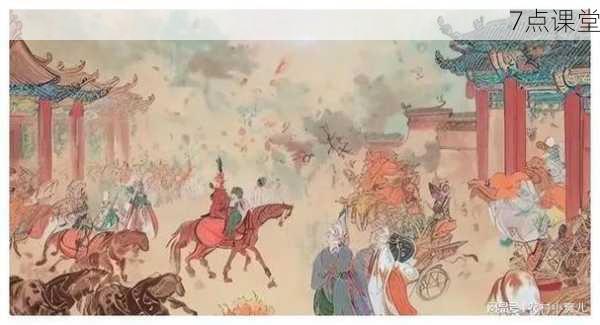在中国文学史上,盛唐诗歌的璀璨星河总令人心驰神往,当我们仰望这片文学星空时,有三颗格外耀眼的星辰始终以独特的排列方式吸引着后世的注目——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三位初唐诗人常被相提并论,在历代文论中形成"三杰"的特殊称谓,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学并称现象,既源于他们相似的文学革新主张,也暗含着特定历史语境的塑造力量,本文将从人生轨迹、文学主张、创作实践三个维度,解析这种并称现象背后的深层肌理。
同途殊归的人生轨迹
三位诗人的人生轨迹在初唐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,王勃(650-676)作为神童闻名于世,六岁能文,十六岁应举及第,却在仕途上屡遭贬谪,最终溺水惊悸而亡;卢照邻(约634-686)早年受邓王器重,后因《长安古意》触怒权贵,晚年贫病交加投水自尽;骆宾王(约619-687)七岁咏鹅传为佳话,却在武则天称帝后参与徐敬业起兵,兵败后不知所终,这种由少年得志到中年失意的生命轨迹,构成了三位诗人共同的精神底色。
史书记载中的细节耐人寻味: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写下"时运不齐,命途多舛"时年仅26岁;卢照邻在《五悲文》中自述"形骸流离,精神恍惚"的境遇;骆宾王在《咏怀古意》中发出"宝剑思存楚,金椎许报韩"的慷慨悲歌,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经历,不仅塑造了他们诗文中的苍凉意境,更在后世文人心中引发强烈共鸣,明代胡应麟在《诗薮》中评价:"三子皆负不羁之才,而俱蹇于时",道出了这种并称的心理基础。
革故鼎新的文学主张
初唐文坛仍笼罩着六朝绮靡文风的余绪,三位诗人不约而同地举起文学革新的大旗,王勃在《上吏部裴侍郎启》中痛陈"龙朔初载,文场变体"的弊端;卢照邻在《南阳公集序》里倡导"言壮而情宏"的创作理念;骆宾王更以《帝京篇》等作品实践其"气骨峥嵘"的艺术追求,这种共同的文学革新意识,构成了"三杰"并称的思想内核。
细究其创作实践,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突破传统送别诗的悲切模式,以"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"的豪迈开创新境;卢照邻的《长安古意》以纵横捭阖的笔法解构宫体诗的浮艳;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借物言志,将咏物诗提升到人格象征的高度,三人的创新实践形成合力,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开辟道路,清代学者何焯在《义门读书记》中精准指出:"王、卢、骆三子,实为陈子昂之前驱"。
风格迥异的艺术特质
尽管被后世并称,三位诗人的艺术个性却各具特色,王勃以"高华"见长,其《滕王阁序》"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"的意境,展现天才诗人的瑰丽想象;卢照邻擅作"宏阔"之语,《行路难》中"人生贵贱无终始,倏忽须臾难久恃"的哲思,折射出深沉的生命感悟;骆宾王则以"遒劲"著称,《讨武曌檄》"一抔之土未干,六尺之孤何托"的檄文,彰显出雄浑的笔力。
这种风格差异在具体作品中尤为明显:同写秋景,王勃笔下是"潦水尽而寒潭清"的明净,卢照邻眼中是"九月寒砧催木叶"的萧瑟,骆宾王心中则是"露重飞难进,风多响易沉"的沉郁,宋人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精辟概括:"王子安如初日芙蕖,卢升之如幽涧松风,骆宾王如宝剑出匣。"
并称现象的历史嬗变
"三杰"并称的形成历经了复杂的演变过程,初唐时期,四人并称的"王杨卢骆"更为常见,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中"王杨卢骆当时体"的诗句,杨炯"愧在卢前,耻居王后"的言论,都印证了这种原始组合,但随着文学观念的变迁,杨炯因其作品相对保守逐渐淡出,其余三人因更鲜明的革新精神被后世单独并提。
明代陆时雍在《诗镜总论》中的论述颇具代表性:"王勃高华,杨炯雄厚,照邻清藻,宾王坦易,然杨终带六朝锦色,故三子特为矫矫。"这种选择性记忆的形成,既与后世对文学革新者的推崇有关,也折射出文学批评标准的嬗变,清代编纂的《全唐诗》将三人作品紧邻编排,更强化了这种并称的经典地位。
文学史坐标中的特殊意义
站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回望,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的并称现象具有特殊意义,他们上承庾信、下启陈子昂,在初唐文学转型期扮演着关键角色,王勃对诗歌意境的开拓,卢照邻对乐府诗的改造,骆宾王对骈文的革新,共同构建起通向盛唐诗歌的桥梁。
这种并称现象也启示我们:文学史的经典化过程往往伴随着选择与重构,三位诗人因其相似的人生境遇、共同的文学追求、互补的艺术风格,最终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凝结为特定的文化符号,正如闻一多在《唐诗杂论》中所言:"他们替盛唐诗人开了一条大道,自己却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。"
当我们在现代重审"三杰"并称这一文学现象时,既要看到历史选择的内在逻辑,也要警惕标签化认知可能带来的遮蔽,三位诗人的人生悲歌与艺术探索,早已超越简单的并称范畴,成为解读初唐文学转型的重要密码,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在诉说:真正的文学革新者,永远在继承与突破的张力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,这种精神,或许比任何并称都更值得后世铭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