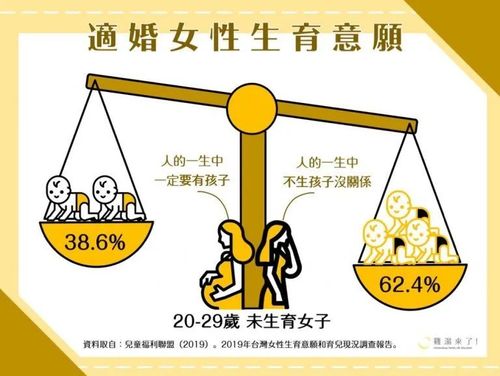深秋微寒,徽州宏村月沼水波如镜,映着白墙黑马头墙的倒影,静谧古老,村里南湖书院旁,一位鬓发如霜的老者坐在青石凳上,对着几个围坐的孩子讲起“徽州玉娘”的故事,孩子们眼神专注,一个女孩微微前倾身体,仿佛要随那故事里坚韧善良的玉娘一同穿越,这方水土上的玉娘传说,如同村前潺潺溪水,在数百年间默默流淌,润泽了一代代徽州儿女的心田。
玉娘的故事,是徽州女人命运的生动寓言,传说中,玉娘是某位徽商家中温婉淑德的女儿,在父兄远行经商之时,她并非深锁于闺阁绣楼之内无所作为,家中账册经营、往来应对,她皆悉心料理,为商贾守好根基,后来父兄遭逢意外,家道中落,她以弱质之躯扛起家族重担,变卖嫁妆维持家计,更以非凡智慧化解家族危难,她的故事里没有烈女传式的惊心动魄,却有着徽州女人在命运风暴里展现出的惊人的韧性、担当与智慧——这正是徽州“贾而好儒”价值观在女性身上最朴素的投射与最坚韧的践行,玉娘形象超越了传统女德教材的刻板,成为一个在现实困境中活出尊严与力量的女性范本。
玉娘传说在徽州得以流传不息,其核心生命力正源于口耳相传这一古老而充满教育智慧的方式,我曾参与一项徽州民间故事的采集工作,在黟县西递、休宁万安等地,发现玉娘故事至少存在七个主要版本,那些在灶台边、油灯下、祠堂前讲述的故事,每一次复述都不是简单重复,讲述者会根据听众——特别是孩童——的年龄、反应,自然融入当时当地的训诫、期许与生存智慧,这种互动叙述,使故事超越了单向灌输,成为一个鲜活的“教育场域”,老人在讲述中自然流露的感叹与评点,如“徽州女人,骨头里是硬的”、“做人要像玉娘,心里有秤”,都是价值观最直接、最生活化的传递。
玉娘传说在徽州女性群体中建构了一种强大的精神认同与行为范式,历史上徽商“三年一归”是常态,徽州女性长期处于实际上的“户主”地位,玉娘作为“留守徽女”的杰出精神代表,为无数现实中的徽州女子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撑与行为参照,她们从玉娘身上汲取力量,恪守“生为夫家人,死为夫家鬼”的训诫,孝养公婆、抚育子女、支撑门户,这种精神力量的塑造,远超生硬说教,它让身处逆境的女性相信,只要持守内心的坚韧与智慧,便能像玉娘一样,在命运的幽谷中辟出生路,守住家族的灯火与尊严,这并非对个体自由的束缚,而是在特定历史境遇下,一种饱含责任与勇气的生存策略选择。
玉娘传说在徽州地区的流传深度与广度令人惊叹,据一项不完全统计,在古徽州“一府六县”核心区域,近80%的村落流传着不同版本的玉娘故事,在歙县棠樾村著名的女祠“清懿堂”中,玉娘虽无单独牌位,但其精神与那些被镌刻铭记的贤孝节烈女性事迹遥相呼应,共同构成了徽州女性精神谱系的重要脉络。
我们今日重拾玉娘传说,绝非为了简单复制旧日规训,其教育启示在于:如何让这些承载着坚韧、智慧、责任感的民间叙事资源,在当代焕发新的育人力量?
在学校教育层面,玉娘完全可以成为徽州乡土教材中的鲜活人物,她的故事可以作为探究徽商文化、传统家族伦理、徽州女性史的生动切入点,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比较玉娘形象与官方《列女传》中女性的异同,思考民间叙事的独特价值与情感温度,在休宁一所小学的实践课堂上,孩子们通过创编玉娘故事的现代短剧,融入了对女性自立、家庭责任的新时代理解——玉娘的坚韧被保留,而她的天地不再仅囿于高墙之内,这种转化,使传统故事成为涵养乡土认同与德性的有效载体。
在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中,玉娘故事更是一座沟通代际的桥梁,长辈在讲述中传递的不仅是故事,更是家族记忆、地方认同与核心价值观念,这种融入日常生活的“叙事教育”,如春风化雨,其效果远胜于空洞的道德说教,玉娘所代表的徽州女性精神——那份在逆境中不折的韧性、为守护所爱而迸发的巨大能量、于琐碎日常中磨砺出的生存智慧——作为一种宝贵的“缄默知识”,在故事讲述的温情时刻,悄然流入新一代的心田,成为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时一份深沉的精神储备。
月光如水,又一次洗亮宏村蜿蜒的石板路,书院旁,老人讲罢玉娘故事,孩子们意犹未尽,一个女孩站起身,学着故事里的玉娘,挺直小小的脊背,眼中闪烁着一种新的神采,玉娘传说,这枚浸润着徽州山水灵性与女性生命密码的文化基因,依然在讲述中被激活,在倾听中被传递。
民间故事的价值,从来不在对遥远过往的复刻与膜拜,而在于那些穿越时空依旧能叩击我们心灵、赋予我们力量的精神内核,当玉娘的故事在当代孩童心中激起回响,这份源于泥土、历经时光淬炼的生存智慧与坚韧品格,便真正完成了从古老叙事到鲜活生命的转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