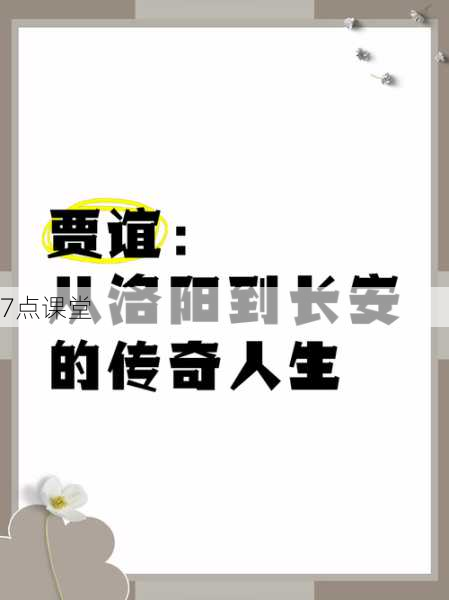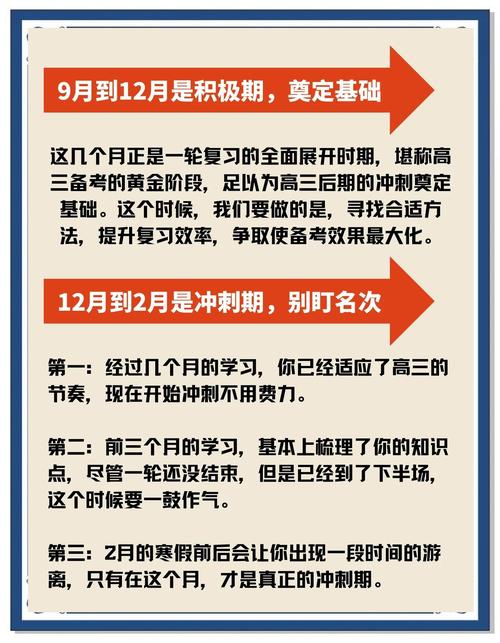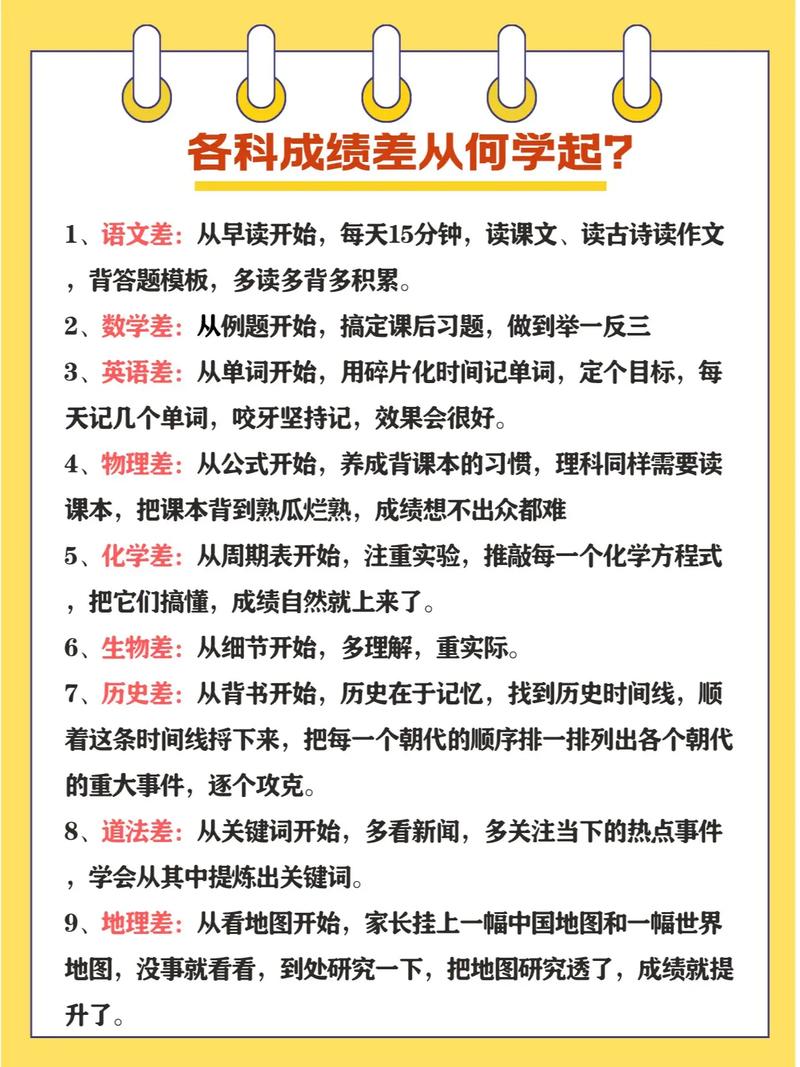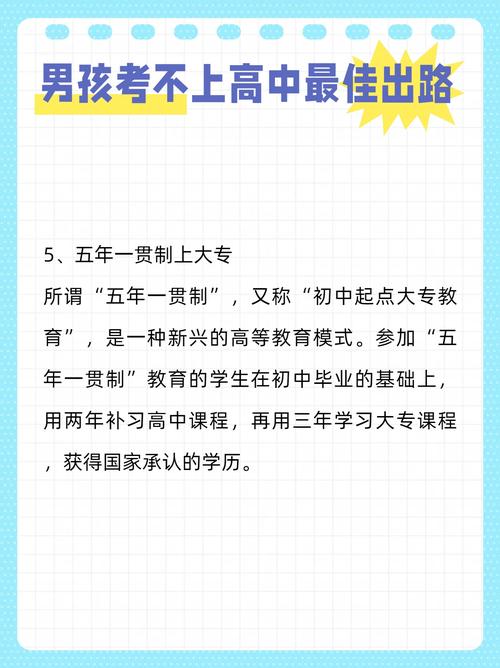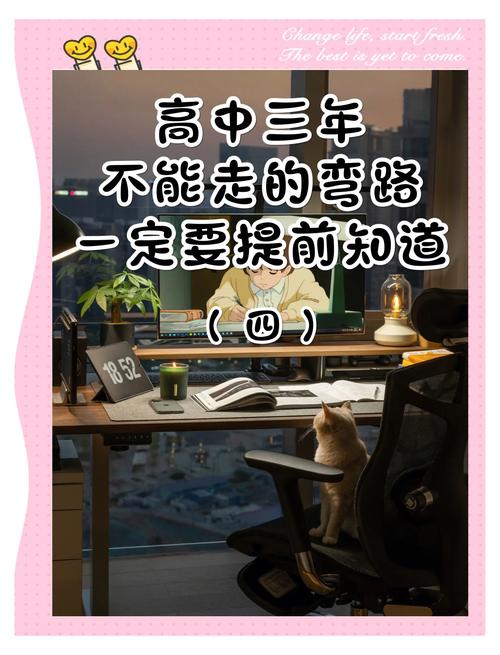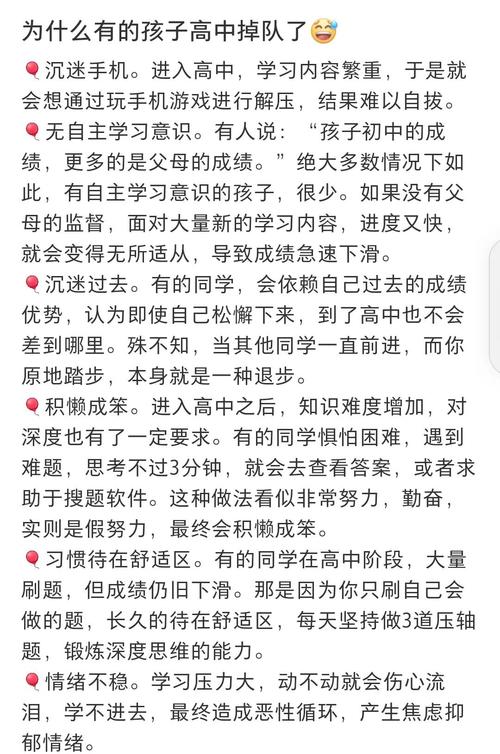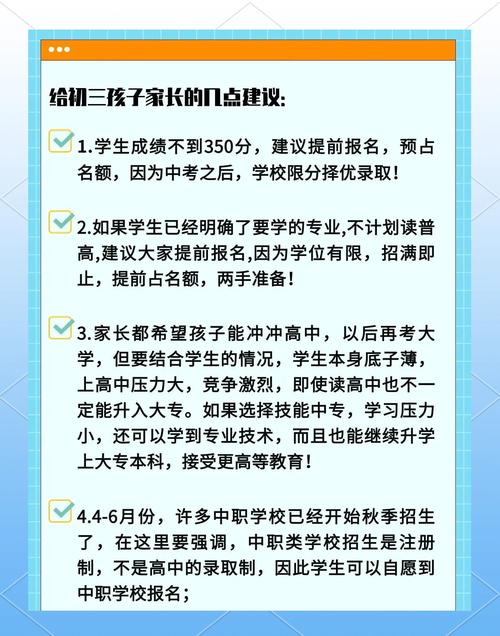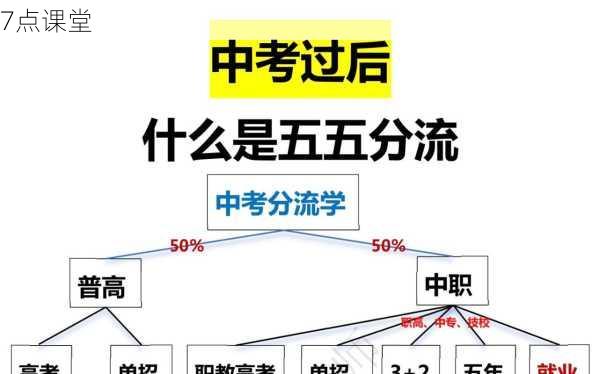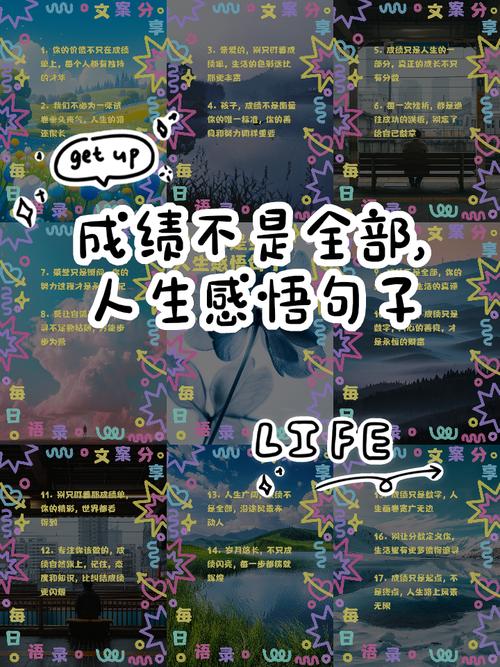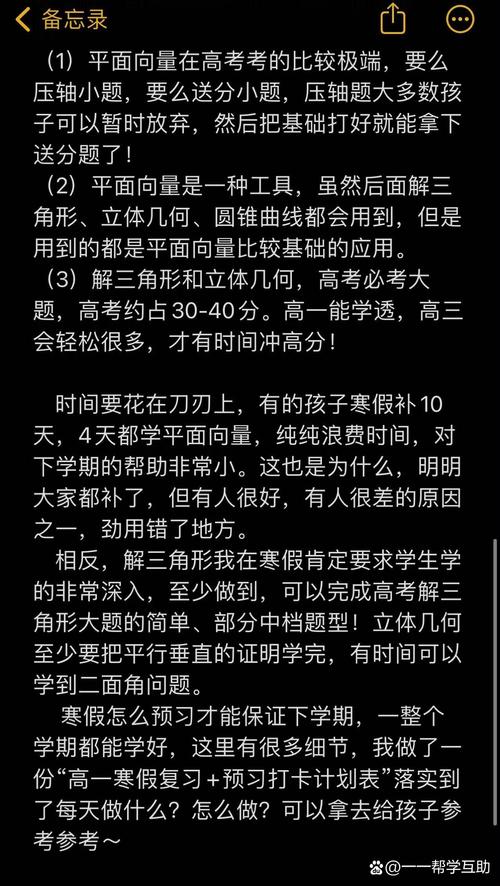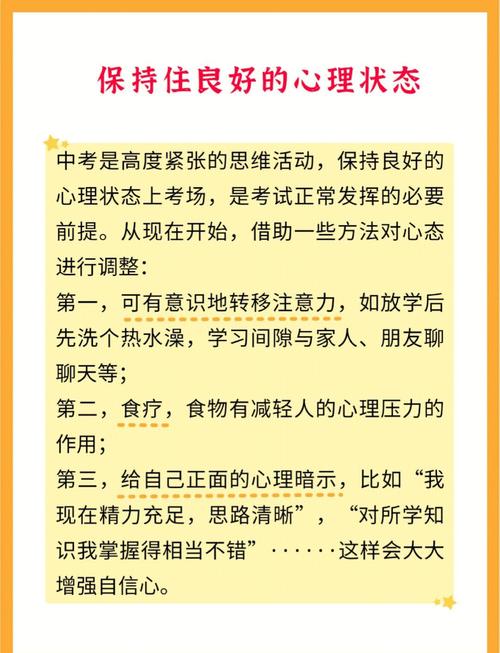横空出世的洛阳奇才
公元前200年的洛阳城,一位注定撼动西汉思想界的青年正在伏案疾书,贾谊出生于商贾云集的河南郡治所,其家族虽非显赫世族,却以诗书传家,史载其"年十八,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",这种早慧在重视经学的汉代社会犹如璀璨星辰,当时主政河南郡的吴公(史失其名)乃李斯同乡,深谙法家治国之道,破格将这位布衣少年纳入幕府,三年间,贾谊协助吴公将河南郡治理为"天下治平第一",这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实践基础。
汉文帝元年(前179年),朝廷开"贤良方正"科,吴公力荐门生,21岁的贾谊以最年轻博士身份入值未央宫,每逢廷议"诸老先生未能言,贾生尽为之对",这种超越年龄的政治智慧,让文帝惊叹"吾不见贾生,自以为过之,今不及也",短短一年间,这位青年才俊连越九级,官至太中大夫,创下西汉升迁速度之最。
改革风暴中的孤独舞者
正值巅峰的贾谊开始推行其政治蓝图,在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》中,他提出"改正朔、易服色、定官名、兴礼乐"的全面改制方案,试图以周礼为蓝本重塑汉制,其《论积贮疏》直指当时"背本趋末"的社会危机,主张"驱民归农"以固国本,这些触及根本的改革迅速引发既得利益集团反弹,绛侯周勃、颍阴侯灌婴等军功集团元老联合诋毁:"洛阳之人,年少初学,专欲擅权,纷乱诸事。"
公元前176年,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,南下途中经湘水凭吊屈原,作《吊屈原赋》自况:"鸾凤伏竄兮,鸱枭翱翔。"在潮湿卑湿的长沙国,他完成中国首部哲学寓言《鵩鸟赋》,借鸟喻理阐述祸福相倚的辩证思想,这段流放岁月虽仅四年,却使其思想完成从法家务实到道家思辨的蜕变。
未央宫中的最后抗争
公元前173年,文帝思念贾谊"召见宣室",这次深夜长谈被李商隐诗化为"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"的经典场景,贾谊借此机会上呈《治安策》,提出"众建诸侯而少其力"的削藩方略,文中"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"的论断,二十年后在晁错削藩引发七国之乱时得到验证。
改任梁怀王太傅期间,贾谊的政治智慧达到新高度,他创设"三表五饵"制匈策略,主张以德政分化匈奴各部,这种超越军事对抗的边疆思想,较之武帝时期的穷兵黩武更具战略远见,当文帝欲封淮南厉王四子为侯时,贾谊冒死直谏:"仇雠之人,不宜得封",这种坚持原则的风骨,连司马迁都赞叹"虽古之伊、管未能远过"。
流星陨落与思想永生
公元前169年,梁怀王坠马身亡,贾谊自认失职,"常哭泣,后岁余亦死",年仅33岁,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结局,为其传奇人生增添悲剧色彩,然其思想火种并未熄灭:晁错继承其削藩主张,董仲舒发展其天人学说,直至武帝时期"推恩令"正是"众建诸侯"策略的完美实践。
贾谊著述今存《新书》56篇,过秦论》开创"史论"文体,那句"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"的论断,成为历代治国者的警世恒言。《大政》篇中"夫民者,万世之本也"的民本思想,较孟子"民贵君轻"更具实践价值,其经济思想中的"积贮"理论,实为后世常平仓制度的理论先声。
历史长河中的多维镜像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将贾谊与屈原合传,凸显其"志洁行廉"的人格魅力,班固《汉书》虽赞其"通达国体",却批评"其术不熟",直到北宋苏轼作《贾谊论》,方跳出"怀才不遇"的传统视角,指出"非汉文不能用生,生之不能用汉文也"的互动关系,这种评价变迁,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价值取向。
当代学者发现,贾谊思想实为儒法道融合的早期范例,他既主张"礼者禁于将然之前"的儒家教化,又强调"权势法制"的法家手段,同时吸收道家"虚舟"的处世哲学,这种思想杂糅,恰是汉初黄老政治向独尊儒术过渡的生动写照。
跨越千年的思想对话
站在未央宫遗址遥想当年,那个慷慨陈词的青年身影早已融入历史烟云,但当我们重读《治安策》中"可为痛哭者一,可为流涕者二,可为长太息者六"的忧思,审视当下社会治理中的央地关系、民生保障等议题,仍能感受到穿越时空的思想共振,贾谊用生命诠释的知识分子担当,正如他在《鵩鸟赋》中所言:"万物变化兮,固无休息。"这种永不停息的思想活力,正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。